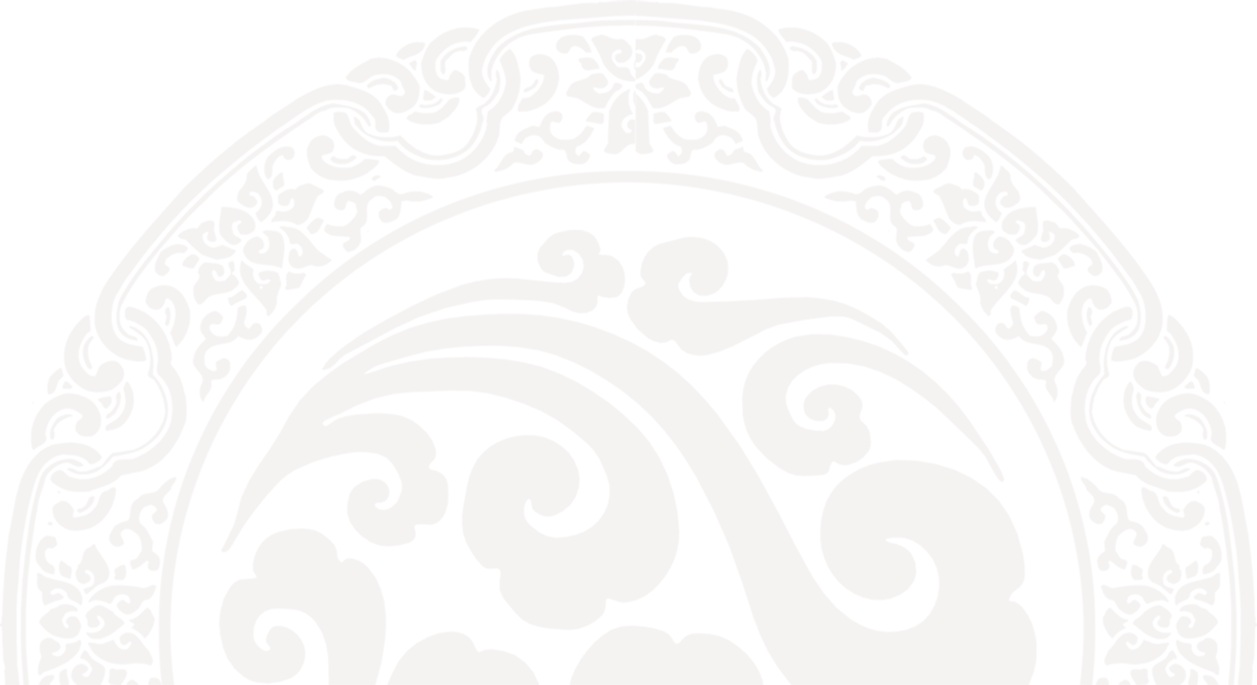
“如果没有经过申遗这8年的宣传和介绍,南京云锦也许早就不复存在了。”当回首8年申遗路,南京市云锦研究所所长王宝林发出这样的感慨。云锦的织造工艺极其复杂,至今仍无法用机器替代。织造时,需要提花工和织造工两人在长5.6米、宽1.4米、高4米的大花楼木织机上默契配合。即使最熟练的夫妻档,一天也只能生产5厘米左右的云锦。和其他很多传统民间艺术一样,南京云锦曾数度面临“人亡艺绝”的险境。
解放初期,有1600多年历史的云锦一度濒临消亡,当时仅剩下4台织机、3位传人。1956年10月,周恩来总理发出“一定要南京的同志把云锦工艺继承下来,发扬光大”的指示;翌年12月,南京成立云锦研究所,致力于云锦技术的传承和保护。1996年,南京云锦再次陷入危机。由于云锦研究所资金匮乏,大量人才流失,设备破损也无法更新,最后只有不足百人在挣扎着维持。“如果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云锦,也许云锦就有了生存的机会!”在苦苦思索中,王宝林萌发了申遗的念头。但是2000年,昆曲申遗的时候,由于根本不懂申报程序,云锦没来得及迈开申遗的脚步。
2002年6月,南京市成立“南京云锦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云锦就此正式踏上申遗路。2002年,云锦第一次入围国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预备清单。但2003年9月,只传来古琴申报成功的消息,云锦和其他3个项目与“非遗”擦肩而过。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的文化官员木卡拉曾到南京考察,当问起当地大学的学生是否听说过云锦时,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上来。木卡拉又上街询问市民,但结果仍然让他失望。
要得到世界的认可,首先要让中国人自己认可。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云锦,当时的申遗领导小组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春晚上展示云锦!尽管心里没有多少底,王宝林还是带着云锦布料上北京找到了2003年央视春晚的总导演金越。云锦因“美若绮云、灿若云霞”而得名,作为元、明、清三朝的皇家御用品自然有着极为不凡的气度。金越一看到云锦布料,当即同意用它制做2003年春晚主持人服装。为春晚四位主持人赶制出的12件华服让更多的中国人见识到了云锦的雍容华贵。
有了第一次的历练,云锦对申报做了更充分的准备,也有了更大的期望。2004年,云锦再次被文化部列入申遗预备清单。可令人万分遗憾的是,2005年,被寄予厚望的云锦再次落选。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前制定的规则,每个国家每两年才能申报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在全世界浩浩荡荡的申遗大军中脱颖而出,其难度的确可想而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的历史非常短,2001年才开始第一次评选,其后的申报评选规则一直在不停地调整变化。云锦的申报材料在8年时间里,就变了三变。比如,第一次申报时,宣传片的时间有2个小时,申报文本字数不限,可以任意发挥;第二次申报,宣传片要求控制在10分钟以内;第三次,申报文本又有了新要求,字数不能超过200个英文单词。如何适应国际规则的不断变化?如何用国际通用的语言推销自己?这是云锦申遗路上绕不开的一个问题。
“你要用外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告诉他们,你为什么是独一无二的。”谈到云锦申遗之路的体会,IOV(联合国教科文—民间艺术国际组织,为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正式机构)中国分会主席陈平这样告诉记者。从去年开始,在文化部外联局官员的促进下,IOV开始参与到云锦申遗的国际运作当中。在考察研究之后,IOV的专家们发现,云锦的申报材料还存在一些“硬伤”:最能体现云锦复杂工艺的一些专有技术,例如“通经断纬”、“逐花异色”等连普通中国人都很难理解的词语却直接用拼音代替;使用了大量华丽的辞藻去叙述历史,却缺少外国人最相信的数据;10分钟宣传片的拍摄方式略显枯燥,很难引起观众的兴趣等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云锦的申遗进程。“我们后来去掉了原来申报材料上的所有形容词,用计算机工作原理类比极其复杂的云锦织造工艺,用最简洁的话语把最实质的内容传达给了评委会。”王宝林兴奋地告诉记者,后来评委们都能够复述出云锦的特点。
2009年9月,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作为中国古老的织锦技艺最高水平的代表,成功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